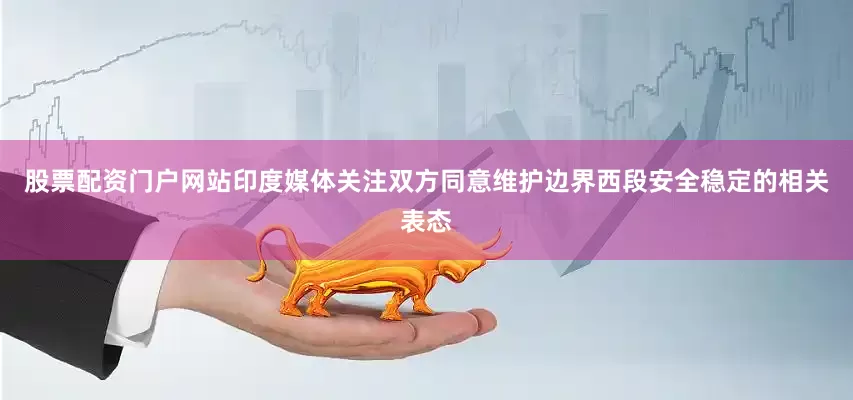1949年8月4日,湖南迎来了和平解放的时刻。解放军第十二兵团接到命令,进入长沙市开展接管工作。司令员肖劲光和政治委员黄克诚正忙于稳定社会秩序,整编起义部队,确保新政权顺利过渡。
当天,在长沙市军管会办公楼门外,一位年迈的农民缓缓走来,神色显得既犹豫又紧张。他站在门口,时不时地用眼角余光扫视着站岗的警卫战士,显得异常焦急。
警卫员察觉老人似乎有急事,便上前礼貌地问道:“大爷,您找谁或者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吗?”
老人犹豫片刻,小心翼翼地开口:“同志,我是来找我儿子的,他乳名叫五伢子,已经离家二十年了。”
展开剩余90%警卫员听罢,面带微笑,耐心问:“大爷,您儿子叫什么名字呢?”
老人回答道:“他叫许德华。”
警卫员认真思索了一会儿,却没听说过这个名字,只能遗憾地摇了摇头。
老人从怀中掏出一张旧报纸,展开后指着上面的一张照片对警卫员说:“这照片上的人,好像就是我们家的五伢子。”
警卫员仔细端详那张照片,神色立刻变得惊讶。虽然报纸印刷并不清晰,但很明显,这正是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的照片。
警卫员连忙请老人进屋,并立即将此事汇报给肖劲光。
肖劲光听后难以置信,亲自召见老人进了军管会办公室。
老人显得既拘谨又激动,肖劲光亲切地问:“老大爷,您刚才说照片上的人是您的儿子?”
老人点头,并再次拿出那张报纸,指着照片详细告诉肖劲光。
报纸报道的是兰州解放的消息,照片正是许光达在兰州向军民发表讲话的场景。
仅凭一位老人的口述和一张照片,肖劲光觉得还不足以确认身份,便指示有人将情况报告给中央军委,请求核实。
不久,中央军委回复了确认电报,证实许光达的乳名确实是“五伢子”,原名许德华,而那位老人正是许光达的父亲,许子贵。
听到这个消息,肖劲光和老人都激动万分。许光达在兰州接到消息后既高兴又愧疚,对父亲的思念和歉疚之情溢于言表。
许光达,原名许德华,190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萝卜冲的一个贫苦农家,排行第五,因此得乳名“五伢子”。
许家世代务农,生活艰辛,尤其是在那个战乱纷扰的年代,家里常常吃不饱饭。
童年时,许光达曾目睹父亲因忧虑家中生计,脸上早早爬满了皱纹,满是愁容,看上去异常憔悴。
他还记得小时候看到一位饥饿的母亲坐在河边,抱着哭喊“妈妈我饿”的幼儿,绝望中抱着孩子跳河自尽的惨烈场景。
这件事深深震撼了幼小的许光达,他奔回家抱着母亲痛哭,从那时起,他发誓无论多么饥饿,也不敢在母亲面前叫喊,怕她因绝望而轻生。
这段痛苦的经历深刻烙印在他的心灵深处,也成为他日后坚决投身革命的强大动力之一。
长大后,因家境贫寒,许光达没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进入学堂,只能偷偷躲在窗外听课,满怀渴望地汲取知识。
父亲许子贵虽知情,却因无力支付学费,只能默默叹息,眼含泪水。
一个寒冷的冬天,许光达帮父母干完农活后跑去听课,不料因天气严寒不觉中冻得晕倒在教室外。
醒来时,是学堂老师邹希鲁将他抱进教室取暖。
邹老师问他为何不进教室听课,许光达含泪答:“我家没钱。”
邹老师被感动,流下眼泪:“孩子,只要你想学,我愿意免费教你。”
听闻此事,许子贵既欣慰又感激,带着许光达去给邹老师磕头感谢。
许子贵明白,只有孩子接受教育,才能摆脱贫穷的命运,不再受欺凌。
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,父母的辛勤付出和老师的无私帮助,成为许光达坚韧不拔的根基。
他努力学习,成绩优异。1921年,13岁的许光达考入长沙师范学校,邹老师也调至该校任教。
邹老师家中遇变,为安顿儿女,与许子贵商议,将9岁的二女儿邹靖华许配给许光达。
这段联姻既是情感的纽带,也象征着恩情的传承,邹靖华后来成为许光达一生的挚爱妻子。
初到长沙时,许光达怀揣着光宗耀祖的梦想,期望通过仕途改变家族命运。
但1923年“六一惨案”亲眼目睹无辜市民惨遭日本军舰士兵射杀的惨烈景象,使他认清现实:仅靠官职和学问无法拯救破败的国家,必须靠革命推翻军阀,才能实现民族独立。
1925年,许光达从师范毕业,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,正式踏上革命征程。
父亲始终无法理解他的选择,多次写信催促回家,均被拒绝。
1927年三河坝战斗中,许光达负伤失联,辗转回家,在父亲安排下与邹靖华完婚。
婚后,他依旧心系革命,因被军阀何键通缉,只得隐姓埋名远走他乡,长达二十余载。
这期间,他无法回家与父母通信,只能默默承受家人以为他已遇害的悲痛。
1937年,邹靖华历经艰辛抵达延安,与许光达终于团聚。
而许子贵至此仍不知儿子安危,直至1949年,意外看到一张报纸照片,才确定儿子仍在人世。
饱经风霜的老人此时仿佛得到了上天最大的恩赐,怀着满腔希望前往军管会求助。
父子终于取得联系,许光达写信诉说对家人的深切思念。
许子贵反复朗读儿子的来信,泪水湿润了双眼。
新中国成立后,许光达调入北京工作,虽日理万机,仍不忘频繁写信慰问家中老父。
他出身贫寒却功勋卓著,一生戎马生涯无私无欲,从未以权谋私,即使面对父亲,也始终保持“铁面无情”的作风。
1950年,许光达难得抽空回乡探望。
他已是官员,亲朋好友纷纷聚集迎接,并提出希望随他去北京发展。
许光达对此震惊,严正声明自己是共产党员,不会带家人“当官发财”,一切为人民服务,非家族利益。
父亲虽不识字,却理解并支持儿子的决定。
这次回乡短暂停留仅十天,许光达便返回北京,从此未再回家。
1957年,90岁的许子贵病逝,按照长沙风俗,子女们需为父亲办盛大丧事。
哥哥致电许光达,催促他回家主持葬礼,并带白布孝服。
得知噩耗,许光达与妻子悲痛欲绝,邹靖华泪流不止,许光达强忍悲伤,踱步屋内。
他与父亲朝夕相处时间极少,脑海中不断浮现父亲期待的目光与劳累的身影。
虽渴望尽孝,许光达却无法接受哥哥要求他回家主持盛大丧礼。
家人希望以豪华仪式彰显家族荣光,但这与中央提倡的移风易俗、简办丧事的政策相悖。
作为中央委员,许光达必须遵守组织规定,不得带头违纪。
他深知若回家,将引来省政府及武装部等多方官员随行,形成排场,容易被群众误解,甚至给共产党形象带来负面影响。
内心虽极为悲痛,却不得不坚决拒绝。
邹靖华体谅他难处,建议自己代为回乡协助办理丧事。
许光达断然否决:“无论是我还是你都不能去,只有派政治干部前往,严格遵守移风易俗。”
最终,他们找了一位熟悉湖南风俗的干部代表前往。
此人到达萝卜冲后,遭遇哥哥强烈质疑:“许光达为何不回?没有他主持,父亲不能出殡。”
家人因许光达未归,情绪激动,已经请来和尚做道场,准备铺张仪式。
政治干部耐心劝说,强调执行中央政策的重要性,但哥哥仍执意要求许光达归家。
当时天气炎热,遗体需尽快安葬,干部无奈打电话给许光达求助。
许光达感到为难,邹靖华再次提出亲自回去,但他坚持:“我们必须树立新风,不允许旧俗抬头。”
经过多方努力,当地党组织和政府派员协商,最终家人妥协,按照简朴要求办理了葬礼,遗体安葬。
丧事共花费150元。
此后,许光达母亲去世,家中再未提出类似奢侈要求。
父母离世,许光达时常思念兄弟姐妹,但对亲属特殊待遇始终严拒。
1960年,国家面临困难,许光达主持会议时要求司令部干部劝阻亲属前来北京探亲,限制探亲时间不超过三天。
未料不久,四哥许德富与六弟许德强突至北京,意欲投靠。
经商议,邹靖华出面劝说二人返乡。
许德富却愤怒反驳:“这里许光达官大,他不说话,谁敢让我们走?”
兄弟二人无奈进了许光达家,发现连首长家中也只能吃藻类代粮,羞愧不已。
两人沉默良久,最终选择返回家乡。
不久,许光达接到电话,得知许德强在安阳车站病倒,情况危急。
许光达紧急派人将弟弟接回北京,途中许德强意识渐弱,抵京后昏迷。
夫妻二人连夜陪伴抢救,但许德强当夜离世。
许光达孤身守候病床,彻夜难眠,满怀懊悔与悲痛。
尸检显示许德强并无大病,乃因长期营养不良,胃部萎缩致死。
乡亲们闻讯痛惜,认为许光达虽身居高位,弟弟却因饥饿而亡。
一向坚强的许光达,抱着弟弟骨灰盒痛哭流涕。
许光达是家族
发布于:天津市在线配资论坛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